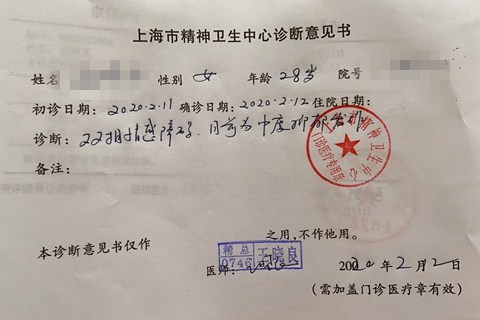【财新网】(专栏作家 魏永征)反对性骚扰,是一个多年的国际性话题,近年在美国兴起所谓me too运动,就是呼吁社会关注此类受害女性。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都有保护妇女、禁止性骚扰的立法(男性也可能遭受性骚扰,此处不论),但是依法治理的难点在于事涉隐秘,取证困难。有的遭受性骚扰的女性诉诸舆论,反而被控诽谤。十多年前有一位女演员发布博客文章称遭受男导演性骚扰,被控侵害名誉权(诽谤),承担侵权责任,我当时就有专文批评。当下又有类似案件,引起舆论关注。
究竟什么是诽谤?
还用问吗?这里不去回溯“微言曰诽、放言曰谤”以及外国“蔑视权贵法”之类的古老历史,就说当下,从学术到日常理解,诽谤就是散布虚假事实贬损他人名誉,并无异议。
中国法律对诽谤作出定义较晚,最初是在1978年《刑法》第145条:“捏造事实诽谤他人”(1997年《刑法》此条序数改为第246条)。1986年《民法通则》有禁止诽谤的规定,而没有具体阐述。只有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在第七问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他人名誉处理。”以及第八问:“(批评)文章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些规定与通常理解一致,就是诽谤侵权行为的基础要件是散布虚假事实。
十多年前我批评的那件诽谤案件的判决书则是这样的措辞:被告(即发布博文称遭受性骚扰的女演员)“对自己文章的内容没有提供翔实的、有效的证据加以证实”,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为性暗示,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
这就有一个问题:虚假与不能证实是不是同一回事?初中学生都会回答你:不。不能证实仍然含有证实的可能性。法律明明规定了失实(虚假事实)构成侵权,判决却说不能证实也是侵权,这符合法律规定吗?
强调一下:我们国家实行成文法制度,判决必须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样超越法律的“法官造法”行为是不合法的。这就是我当年批评这件判决的基本立论。
如今的《民法典》第1025条以排他性的穷尽列举规定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的三种侵害名誉权行为:一是捏造、歪曲事实;二是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是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说排他性穷尽列举是指,按此条规定,除了这三项之外,其他情况都“不承担民事责任”。这里一、二两项,从法理上说就是诽谤,前者是故意的,后者则出于过失。这条规定,是中国四十年来审理诽谤等侵害名誉权案件的总结,属于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效力远远高于以前的司法解释,司法机关理应不折不扣切实执行。
禁止性骚扰,从2018年《妇女权益保护法》到如今《民法典》都有明文规定。受害当事人及其同情者通过舆论揭发性骚扰,符合公共利益,具有舆论监督性质,这个道理这里不用多说。
但是在近来在微博揭发性骚扰引发侵害名誉权纠纷的一件案件的一审判决中又见到这样措辞:
……二被告(其中一位是自述受害女性,另一位是发布同情文章的评论人——引注)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亦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其所述情况真实存在。故在二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其陈述为真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法院以此判决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这就同十多年前的那件判决有异曲同工之嫌。不能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真实、缺乏事实依据是不是就等于捏造事实、等于言辞严重失实呢?为什么不敢直截了当指二被告捏造事实或言辞严重失实呢?就算本案在时效上还不能适用《民法典》条文,但是也不应当公然与《民法典》的规定相背离吧?何况还有1993年的司法解释呢。
我不否认,当然可能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意图,借揭发性骚扰之名,捏造、歪曲事实,以求一逞,对此应该绳之以法;但是应该坚持查明事实,依法办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司法机关自身不能依法判案,甚至超越法律,也是必须纠正的。
中国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变迁
不过话说回来,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也确实自有难处。这就是性骚扰行为通常十分隐秘,除非完成性侵,一般的调戏、猥亵乃至性侵未遂,很难留下可见的痕迹,即证据。而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还有一条:揭发性骚扰引发的名誉权案即诽谤案与通常侵权纠纷不同:通常侵权纠纷控方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辩方反驳控方主张则要证明控方所举的事实不存在;诽谤案件则相反,控方需要证明对方散布的事实不存在,辩方则需要证明揭发的事实存在。那么究竟主要应该由何方承担证明的责任呢?
实体法问题就这样延伸到程序法问题,这里简要回顾中国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历史。
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先于实体立法,1982年就制定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原则(中国民事证据制度,还有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收集调查证据而实际上以后者为主发展到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有限地接受当事人请求调取证据这样的演进,此处从略)。但是法律并未规定控辩双方应由何方就判决结果承担举证责任,这样在1986年《民法通则》实施后,在一时勃兴的新闻侵害名誉权纠纷中就发生了“谁主张、谁举证”还是“谁报道、谁举证”的争议,若干法院在接受控方新闻失实、侵权的投诉后,就要求辩方(新闻记者或单位)证明新闻真实,后者不能证实就判决败诉,构成侵权。新闻业界和学界有些人士对此提出强烈异议,认为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于法无据。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了六类由被告负责举证的案件其中并不包括诽谤纠纷案件之后,在诽谤诉讼中将内容是否真实的举证责任倒置于辩方的做法仍然相当普遍。
此后民事举证责任制度发展有三个重要的关节点:
第一个关节点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中第2条以两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和“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前一款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诉辩双方都要就自己的主张举证,法理称为行为意义上或过程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后一款是指双方都履行举证责任之后尚不足以证明本案所诉求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后果,法理称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本“规定”第4条又在1992年“意见”基础上规定了八类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件,应该理解为除此八类,皆应由原告即控方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许多场合下所说的举证责任,都是指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但是2001年的这个“规定”第7条又赋予法院在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给法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留下一个回旋空间,成为法院在审理诽谤案件中自行确定辩方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重要依据。
据张鸿霞博士在2010年对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至2009年270件名誉权案件统计,除去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和侮辱性质案件之外的93起案件中,原告就内容虚假、被告具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5起,占5.4%,被告就内容真实、主观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86起,占92.5%。
第二个关节点是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第90条重申了2001年“规定”第2条而略有修改,第91条在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前提下就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作出两项规定:(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第二项当然包括了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应该就受到对方散布虚假事实侵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2009年《侵权责任法》明文规定了过错责任、推定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以及后两种情况应该以法律规定,从第四章起全面规定了各种特殊案件的举证归责原则,所以这件“解释”就无须再就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作出专门列举规定。众所周知,《侵权责任法》所列特殊举证归责原则的范围并不含有名誉权等人格权纠纷一类案件。有关内容如今纳入《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
第三个关节点是2020年5月实施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新“规定”以自认制度、书证制度、鉴定人制度等为主要亮点,不再有2001年“规定”第7条那样的由法院确定举证责任的条款,也就是取消了法院在一定范围内举证责任的分配权。
这就意味着,依照法律规定,在民事诽谤案件中,控方应举证证明所指诽谤内容虚假,辩方则应证明内容真实,即双方都履行过程意义的举证责任,如果经过双方举证,内容假真仍然不能确定,即不能证明虚假,则应由承担结果意义举证责任的控方承担不利后果,即败诉。
顺便再提一下:《民法典》有关内容严重失实而侵害名誉权的规定(即如今的第1026条)自2018年起前四稿在规定六项“合理审核义务”之后都列有“行为人应当就其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条文,在2020年提交全国人大的审议稿中被删除而正式通过。表明诽谤案件证明过错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事实真伪的证明当然更谈不上倒置了。
中国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业已引进认定案件事实的盖然性原则,成文规定如2014年“解释”第108条。看得出前引微博揭露性骚扰引发的名誉权案件的判词是意图运用这个原则的。但是根据条文,首先应该就负有举证责任(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交证据进行审评,即指出诽谤案件的控方主张事实不存在的证据表明具有高度可能性,现在却单指辩方提交事实存在的证据不能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而只字不提控方主张的情况,这就难免“画虎不成”之憾。
由于新“规定”实施还不到一年,有些法院还在按旧规对某些案件自行确定举证责任,旧规实施20年,有了惯性,一时改不过来,可以理解,但是应该指出这种做法已经没有法律依据,是超越法律规定的。就如前述判决书所言:
行为人(指二被告——引注)需就其陈述的真实与否负举证责任,若其不能证明所述为“真”,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这种表述不应该再出现了。
法律并不是万能的
人们业已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增加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的案由,就是说,性骚扰受害人也可以就此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正如我在十多年前那篇文章中指出,性骚扰受害之诉(那时还只是假设)与揭露性骚扰引起诽谤之诉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性骚扰受害人作为控方负有举证责任,不能证实性骚扰存在则败诉;后者被指性骚扰嫌疑人负有举证责任,不能否定性骚扰存在则败诉。
如果性骚扰受害人在性骚扰损害之诉中由于证据不足而败诉,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要是此案被告反过来对原告公开发表揭露性骚扰的言论提起诽谤之诉,就必定胜诉呢?
不见得。
在很多情况下,性骚扰的事实往往处于若明若暗、若有若无的状态。性骚扰之诉不能证明事实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实的虚无,性骚扰案的辩方一旦转化为性骚扰诽谤案的控方,就负有结果意义上证明事实虚无的责任,如果举证不能,或者还不能达到盖然性要求的水平,那么他也不可能在起诉诽谤案中胜诉。
同样的道理,如果性骚扰诽谤案的控方因为不能证伪而败诉,也并不意味就是认定他实施了性骚扰,而应由性骚扰损害纠纷案件来依法裁判。
一般说,两造相争,必有一败。如果发生此类双方都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难道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吗?不是。正如古语提及法律时所云:“网漏吞舟之鱼”,法律也有管不着的地方,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执法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的,时过境迁,事实湮没无闻,是常有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况,法律就无能为力了。
这就要说到名誉,《民法典》已经下了正式定义:“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任何人都在社会中生活,特别是所谓“公众人物”,特别是如今网络时代,一举一动几乎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社会评价与舆论密切相关。回顾四十年来名誉权案历程可以发现:固然大多数案件都收到分清是非、澄清真相的效果,但是也有有的人胜诉了,而舆论仍然会列举他的种种劣迹,说明胜诉纯属侥幸,其名誉反而进一步下降;有的人败诉了,而舆论却会指出其中的种种奥妙,说明败诉值得同情,其名誉反而得到提升。恕我不能举出这些具体个案和人物,以免弄不好招惹官司上身。
我只是想说,每个人的名誉是由他自己的行为书写的,而维护舆论的畅通,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根本条件。■
本文原载《青年记者》2021年5月号,作者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