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文章

美元周期:宿命与抗争
美元指数最终会怎么走,取决于周期宿命与抗争力量之间的博弈
2025年04月29日 10:53


二阶变量视角:股市如何映射经济周期
从金融看经济的角度,资本市场的反应映射了特朗普政策将对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造成极度的伤害
2025年04月07日 09:43


特朗普衰退?还是衰退的周期回归?
伴随其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且表现出高度不确定性,“特朗普冲击”带来的信心提振效应逐渐消退,“特朗普幻象”消退,美国经济再回短周期下行通道
2025年03月24日 09:38


加码宽财政
对刺激经济来说,宽货币只是保健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宽货币”政策要想取得预期作用,需要“宽财政”政策的配合
2024年10月25日 15:48


美国正遭遇一次非典型经济短周期
外生因素扭曲了正常的市场化运行逻辑,引起美国经济短周期波动的市场化内生动力的主导作用严重弱化
2024年10月08日 10:53


银行净息差何时止跌触底
决定利率走势的不是央行,而是资本回报率;生产过剩加剧了本轮净息差收窄
2024年05月09日 1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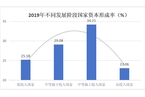
消费拉动是经济增长新模式吗
到底靠消费拉动还是靠投资拉动?增加有效投资是协调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稳定的一致性的重要纽带
2024年04月23日 14:51


周期为什么不见了
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2024年03月13日 14:59

新一轮库存周期或已重启
中国库存周期的拐点或已出现,实体企业补库存初现端倪
2023年10月26日 10:57


PPI触底反弹背后
中国PPI7月出现触底反弹迹象,预计同比降幅将延续收窄趋势,直至跨过负值区间,走出通缩,转向通胀
2023年09月08日 12:21


美国经济何以抗住加息重压
资本流入与制造业回流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幅加息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2023年07月28日 15:15


是什么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
中国以美元结算为主的国际贸易规模变化才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的关键因素,美国需求波动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趋势性变化
2023年06月30日 14:39


疤痕效应下的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将延续复苏,但在疤痕效应下,复苏过程将更为缓慢、持久
2023年06月09日 10:54


系统论视角看经济运行
在分析经济运行时,要关注“风”,识别“风”,度量“风”的影响,更要关注经济体系自有的“季节”。只有这样,才能在观察经济时,既看到数据升降之“形”、市场变化之“态”,又看到经济发展长期之“势”
2022年11月21日 14:30

在不确定中把握投资的确定性
今年投资环境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三大不确定性:一是全球疫情反复带来的供给冲击;二是中美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错位,对“以我为主”的宽松政策可能形成掣肘;三是信用创造条件发生了变化,可能对信用扩张形成约束
2022年07月19日 10:41

货币供给、通货膨胀与货币流通速度
引发通货膨胀与否,不仅要看货币供给量,还要看货币流通速度,特别是在病毒大流行这样的非正常时期
2022年04月15日 17:58

经济复苏与债券市场走势
中国经济需求波动已触及短周期底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概率也已触底,上行趋势确立
2022年03月21日 14:36

美国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加速,能否打破
工资—物价螺旋上升一旦形成,对于哪个国家的央行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和70年代初美国都陷入工资-物价螺旋上升通道,随后的通胀治理令两国政府与央行苦不堪言
2022年03月15日 16:50


重新思考为何美国通货膨胀大超预期
美国本轮大通胀和其他历次通胀一样,都是由消费市场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这样的共性原因造成的,但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超低利率、货币超发、工资—价格螺旋引起需求快速膨胀,劳动力短缺、供应链中断导致供给恢复受阻
2022年03月04日 15:30

利率走势何时反转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国债收益率变动有与经济短周期现象相仿的周期规律性。我们认为,流动性及以GDP增速为代表的经济基本面之外的短周期才是引起中国国债收益率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
2022年01月25日 17:02

加载更多

刘晓曙
刘晓曙,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博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曾任职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总行。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学术关注: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
专栏最新文章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