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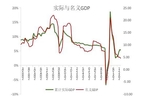
2024年:经济增速4.5%要好于5%
片面强调经济量的增长可能是结构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只有戒除“增速饥渴症”才有机会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2023年11月30日 12:47


经济隐忧与政策抓手
设定增速后的解题过程,从中国经济20年发展经验来看,会表现为严重的结构性补贴和过度的产业政策
2023年07月17日 14:24


从预期扰动看长期资金配置
长期资金并不是只见森林,实现任何收益目标,具体而更短期的路径至关重要
2023年05月25日 16:17


金融加速器启动期待新一轮市场化供给侧调整
在一季度贷款余额同比多增3.1万亿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认为通胀可能相对滞后,因此对中国经济保持相对乐观一些?
2023年04月25日 10:41


如何应对放开过程对经济的进一步冲击
为推动经济尽快平衡地恢复到正常状态,放开疫情防控是一方面,防止放开的过程对经济的进一步冲击同样重要
2022年12月15日 10:41

2022:黑天鹅与灰犀牛
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主要是美国的紧缩周期、地缘政治和经济危机;灰犀牛则是债务和人口
2022年01月28日 09:22

跨期调节的政策含义
国内对跨周期调节普遍理解为相对于逆周期调节的新“事物”,但实际上“跨周期”并没有改变政策的“逆周期”本质,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体现在调节的力度和目标的变化
2021年09月01日 11:40

稳定杠杆率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过去保持债务可持续性的方法,即债务水平的货币化难以为继,因为货币化是以平均无风险利率维持在高位实现的,它造成政府债务上升挤出私营经济,这是杠杆率与经济实际增长水平可能负相关主要原因之一
2021年07月09日 16:24

深情回望2020
怀着对未来的温暖期冀,在岁末年初以及未来的日子,我们应时时深情回望,以回报那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瞬间
2020年12月31日 17:46

货币政策的传导与不平等的社会效应
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货币政策的利率空间都还有较大的余地,在未来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甚至是未来全球经济面临危机时都可能寻求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因此应当尽量减小货币政策的财政功能,减少扭曲和不平等带来的效率损失,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以迎接更多的挑战
2020年11月30日 10:16

内循环的边界与应对
内外循环的提出很有意义,我们需要厘清:对于开放经济体,外循环的逻辑是主动出去交朋友,内循环的逻辑是开门迎客
2020年08月12日 10:24

央行如何改进货币政策指引
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增长阶段,财政和货币政策也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长期手段。比如财政更加注重二次分配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措施,而货币则脱离短期经济增速,提供与长期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利率条件
2020年07月25日 09:55

财政、货币、央行独立性与救疫
未来中国央行和财政部的配合有没有可能更密切?这依赖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和财政在经济增长中角色的转变
2020年06月10日 11:55

2020中国宏观经济的点与面
稳增长多立足短期,最容易的就是回到经济旧有的增长模式上去,而看不到应有的产业结构调整
2019年12月24日 16:56

怎么看待中国的杠杆效率
中国杠杆率激增却没有稳住经济增速,代表着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以某种资产形式沉淀下来,这可能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也是杠杆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9年09月10日 09:49


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未来
加入国际产业链并不是为了贸易顺差,经由国际分工能够获得的是国际信用能力,和在国际产业链上持续的研发能力
2019年06月04日 14:56


金融业占比与经济症结
波动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如果人为熨平这种波动,人们对风险将会茫然不知
2018年11月02日 17:14

改革开放四十年,呼唤全面供给侧改革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对生产要素的改革,在真实经济中对产出有影响的所有要素:个人、企业和制度,这三者的改革应当互相配套,缺一不可
2018年08月31日 13:58

双边机制下的中国国际关系
制度有根本区别的国家怎么样通过双边机制取得平衡是决定未来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
2018年05月02日 11:02

从储蓄到投资
不同的金融系统中,储蓄转化为货币的效率有高有低。好的金融监管总是能对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证货币化的程度适中,既能对投资形成有力支持,又不至于损害到金融系统的稳健性
2018年04月08日 16:49

加载更多
专栏最新文章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